![]() 当前位置: 电商培训 > 电商培训资讯 >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义
当前位置: 电商培训 > 电商培训资讯 >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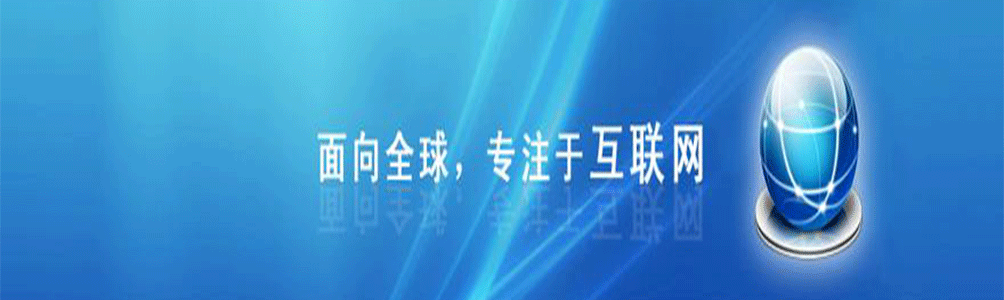
![]() 当前位置: 电商培训 > 电商培训资讯 >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义
当前位置: 电商培训 > 电商培训资讯 >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义
熊英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平台,通知+删除,连带责任
历经三次公开征求意见、四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并于年1月1日生效实施。《电子商务法》全文共七章八十九条,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义务、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与履行、电子商务的争议解决、电子商务促进和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其中关于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义务和责任部分,还具体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义务与责任。本文以《电子商务法》规定为限,分析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的具体义务及其民事连带责任。其间,笔者将《电子商务法》中的规定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比较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期抛砖引玉。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通知+删除”义务
(一)“通知+删除”义务的含义
“通知+删除”义务原本是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要求,即网络服务提供商并不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但如果具体的网络服务商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权利人就会将侵权情况通知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则应在接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后,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删除侵权信息,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则对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行为后果不承担责任,否则依法将与网络服务商即直接侵权行为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通知+删除”义务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1]中有明确规定。由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与网络服务提供商在网络经营活动中的地位具有相同性,因此《电子商务法》也明确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通知+删除”义务。
(二)“通知+删除”义务的履行
1.采取必要措施和转送侵权通知的义务[2]
接到通知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平台经营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是因为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的经营者具有类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一旦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权利人第一时间通知平台经营者,将更有利于对知识产权的及时保护。根据《电子商务法》第42条的规定,平台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认为,“及时”是指在接到“侵权通知”后工作开始的第一时间采取必要的措施;“必要措施”是指平台经营者应该在接到“侵权通知”后,根据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形和权利人的请求,选择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不同措施,即应有针对性地采用有效措施。
转送侵权通知的义务。知识产权权利人通知平台经营者不是因为平台经营者的行为侵权,而是认为平台内的经营者行为侵权。因此,平台经营者接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后,一方面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与此同时应将“侵权通知”转送到平台内的经营者即具体的侵权行为人,便于平台内经营者接到“侵权通知”后,知道自己行为的侵权性,及时终止侵权行为,或举证抗辩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存在侵权。
2.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转送、告知、终止或解除所采取措施的义务[3]
声明转送的义务。平台内经营者接到知识产权侵权通知后,如果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存在侵权,平台内经营者也有权做出“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平台经营者接到平台内经营者“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后,也应及时将“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转送给知识产权权利人。
告知的义务。即平台经营者在将平台内经营者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转送给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还应告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向有关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是因为平台经营者只是一种特殊的“中间人”,没有解决侵权纠纷的司法权力和行政管理的权力。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如果双方不能协商解决,最终也只能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法院依法处理。
及时终止或解除所采取的措施。平台经营者依法履行了“转送和告知”义务之后,“在转送声明到达知识产权权利人后十五日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起诉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电子商务法》如此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正当合法经营的平台内经营者的权益。因为,如果知识产权权利人在接到“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之后,既不投诉也不起诉,说明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有事实依据,那么,平台经营者则应对平台内经营者采用的措施予以终止或解除,恢复平台内经营者的正常经营活动。
3.及时公示“通知、声明及处理结果”[4]
平台经营者作为“中间人”,在接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平台内经营者提交的不存在侵权的声明以及最后的处理结果等都应及时在平台上予以公示。我们认为:这里的处理结果应该仅限于通过平台经营者的中介沟通,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问题的解决情况,不包括行政或司法机关的处理或裁决情况。而要求及时公示“通知、声明及处理结果”的意义在于:一是将有关信息对争议双方透明公开,有利于公平公正地解决双方纠纷;二是有助于提醒平台内其他经营者,经营活动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尊重并保护他人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5]
(一)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的义务
一般来说,平台经营者没有义务审查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是否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但是如果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6]。显然这一规定也是借鉴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规定。
1.“红旗原则”在不同法律、条例、司法解释中的规定
前述《电子商务法》规定的“采取必要措施和转送的义务”其实就是“避风港原则”的适用。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义务”,则是“红旗原则”的适用。在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红旗原则”适用时,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有明确规定,年公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第3项规定、第23条和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也有明确规定。《电子商务法》第45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2.“红旗原则”在不同法律、条例、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差异
从以上规定来看,在适用“红旗原则”时,对网络服务提供商主观上的要求用语不同,从“明知”到“明知或应知”再到“知道”“知道或应该知道”。其实,“明知或应知”等同于“知道或应该知道”,而“知道”可以分为“知道或应该知道”。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要求的是“明知”外,其他规定都可以理解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存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义务。
3.“红旗原则”所要求的“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理解
所谓“知道”应理解为应当知道,即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平台经营者应该知道。例如,根据知识产权权利的侵权通知已经确定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构成侵权,而后被终止交易。但是在侵权纠纷处理后不久,平台内经营者又进行同样的侵权行为,在此种情况下即便没有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平台经营者也应该知道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是侵权行为,应该主动对平台内的经营者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
所谓“应当知道”,也应根据一定的事实推断。假设平台内经营者销售侵权商品,被消费者向平台经营者投诉,之后平台内经营者继续销售侵权商品,应推定平台经营者“应当知道”,并应主动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侵权行为。
(二)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
如果根据具体的情况可以认定,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平台经营者并不当然就与直接侵权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其尽到了“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即如果平台经营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制止了侵权行为的继续,则不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平台经营者依法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履行具体义务的连带民事责任
平台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不是直接实施了侵权行为,而是因为没有及时地依法履行义务导致损害后果的扩大,那么仅仅就损害的扩大部分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显然,平台经营者的连带责任是其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结果,而且连带责任的范围也限于其未依法履行义务所导致的后果。
(一)未履行“通知+删除”义务的民事连带责任
未履行“通知+删除”义务的民事连带责任,也即未履行转送侵权通知、不侵权的声明、必要措施的采取或终止义务的民事连带责任。[7]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并通知了平台经营者,那么平台经营者接到通知后,一方面要及时将侵权通知转送给平台内经营者,另一方面应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免侵权行为后果的扩大。如果平台经营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就损害的扩大部分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平台经营者依法应将平台内经营者不存在侵权的声明转送至发出侵权通知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并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如果最后确认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不构成侵权,那么平台经营者因没有履行以上法定义务,导致平台内经营者的损失,平台经营者应该与错误通知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承担连带的民事责任。
(二)未履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采取必要措施义务的民事连带责任[8]
未履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采取必要措施义务的民事连带责任,是指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我国《电子商务法》已经实施,在今后的实务中如何认定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必将是难点之一。其实在《电子商务法》颁布之前,就有相关的案件发生。
例如,在“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诉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杜国发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9]中,作为该案的第二审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综合客观事实,认为:
首先,在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衣念公司从年起就淘宝网上的商标侵权向上诉人淘宝公司投诉,而且投诉量巨大,然而至年11月,淘宝网上仍然存在大量被投诉侵权的商品信息,况且在上诉人删除的被投诉商品信息中,遭到卖家反通知的比率很小,由此可见,上诉人对于在淘宝网上大量存在商标侵权商品之现象是知道的。
其次,被上诉人的投诉函明确了其认为侵权的商品信息链接及相关的理由,虽然被上诉人没有就每一个投诉侵权的链接说明侵权的理由,或提供判断侵权的证明,但是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提供了相关的权利证明、投诉侵权的链接地址,并说明了侵权判断的诸多理由,且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持续投诉多年,其所投诉的理由亦不外乎被上诉人在投诉函中所列明的几种情况,因此上诉人实际也知晓一般情况下的被上诉人投诉的侵权理由类型。
再次,在案的公证书表明被上诉人购买被控侵权商品时,原审被告杜国发在其网店内公告:“本店所出售的部分是专柜正品,部分是仿原单货,质量可以绝对放心……”,从该公告内容即可明显看出杜国发销售侵权商品,上诉人在处理相关被投诉链接信息时对此当然是知道的,由此亦能证明上诉人知道杜国发实施商标侵权行为。
最后,判断侵权不仅应从投诉人提供的证据考查,还应结合卖家是否反通知来进行判断。通常情况下,经过合法授权的商品信息被删除,被投诉人不可能会漠然处之,其肯定会作出积极回应,及时提出反通知,除非确实是侵权商品信息。故本案上诉人在多次删除杜国发的商品信息并通知杜国发被删除原因后,杜国发并没有回应或提出申辩,据此可知杜国发实施了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
综上,法院认为,上诉人淘宝公司知道原审被告杜国发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商标侵权行为,但仅是被动地根据权利人通知采取没有任何成效的删除链接之措施,未采取必要的能够防止侵权行为发生的措施,从而放任、纵容侵权行为的发生,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帮助了杜国发实施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
通过该案不难看出,判断平台经营者是否存在主观上“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的过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如果通过事实分析,能够合理认定平台经营者存在主观过错,并且也没有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主动采取制止措施,因此导致侵权行为损害后果的扩大,那么,平台经营者就应与平台内经营者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注释:
1.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于年5月18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号公布,根据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修订。该《条例》共27条,自年3月1日起施行。
2.参见《电子商务法》第42条。
3.参见《电子商务法》第43条。
4.参见《电子商务法》第44条。
5.参见《电子商务法》第45条。
6.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第3项、第23条、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年和年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没有变更该规定)和《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
7.参见《电子商务法》第42条。
8.参见《电子商务法》第45条。
9.《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诉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杜国发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年第1期(总第期)。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杂志总第期
IP扫描
转载请注明:http://www.chinatoystradenet.net/dspxtd/14388.html



